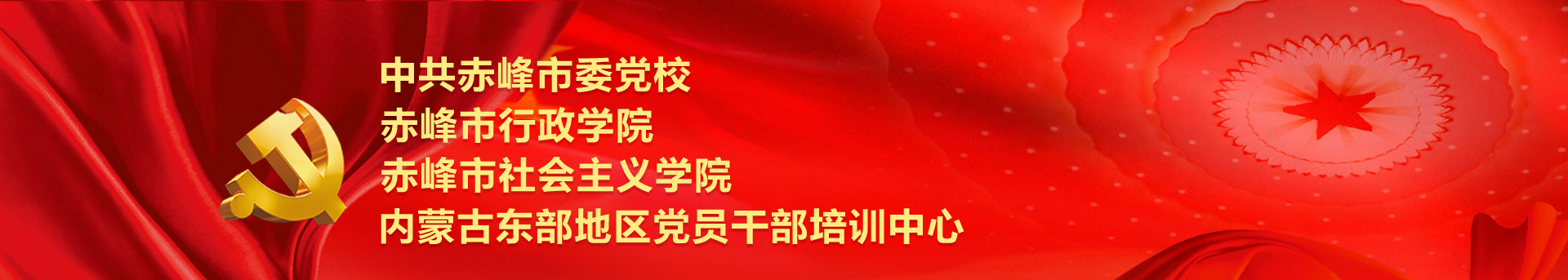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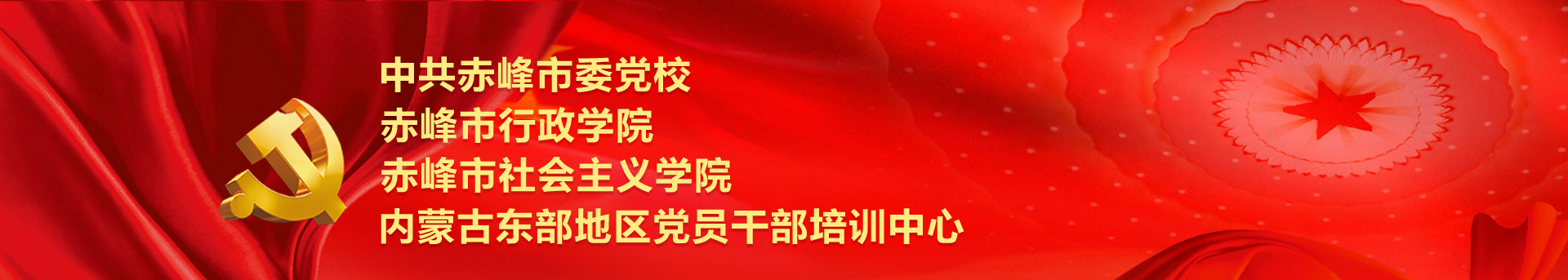
石仲泉,1938年5月生,湖北红安人。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参加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
采访组:您一直提倡“走走党史”,从考察中央苏区开始基本走完了长征路。请谈谈一路走来的感悟。
石仲泉:“走走党史”是我调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后提倡的。那时胡乔木提出党史编写要有生动的场景描写,把历史过程写生动,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一要求做到很难,原因之一是党史工作者缺乏对党史的实际体验。我逐渐萌生了这样的理念:党史工作者应有一个由概念党史经过体验党史,形成形象党史,再来叙述和理论党史的过程;党史工作者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现场,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一般地说,经历了一番体验而写的党史、军史、革命史,不会是文山会海,而是有具体材料、生动情节的;不会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不会是干巴的,而是鲜活的,让人喜闻乐见的。
为什么“走走党史”要从走长征路开始?这和我的长征情结有关。在中学时代,就爱听老师讲长征故事。在研究生期间,当看了《长征组歌》演出,对红军长征异常神往。我没想到后来会在党史部门工作,将来会走长征路。既然研究党史,而且有了“走走党史”的想法,就有了怎么走的问题。如果说青年时代对长征的向往是感性的,那么研究党史以后,对长征的理性认识就对我“走走党史”从何走起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是百年党史最惊心动魄、最精彩感人的篇章。红军长征是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空前考验。这段历史不能忘却,还应大书特书,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因此,在当年“走走党史”时,我决定首先要走走长征路。
在2003年至2005年间,基本走完了中央红军长征路,还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段。2013年还专门考察了西路军血战河西的悲壮历程。这样,我就基本实地考察了红军长征全过程。由此在宏观上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对长征历史和长征精神有了许多在“书斋”里不可能得到的新认知。
采访组:您曾讲述过党史上的三次“重要对谈”,并由此谈到“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请您谈一谈具体情况。
石仲泉:这是党的建设的一段重要佳话。我在2010年发表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一文中,形成三次“重要对谈”的认识。提出三个“对谈”概念,则是在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之后。总书记到西柏坡考察时指出: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深刻领会“两个务必”,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受此启发,我写了篇《“两个务必”与“三个对谈”》时评,将毛泽东与郭沫若关于《甲申三百年祭》信函往来的笔谈称作“甲申对”,与此前的“窑洞对”“赶考对”,合称为三个“对谈”。
先讲“甲申对”。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重要历史关头,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重庆的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于1944年3月发表。郭文着重论述了300年前的甲申年,艰辛奋战18个春秋打天下的李自成农民军在攻陷北京城灭亡大明王朝后,花天酒地,沉沦享乐,结果坐天下不到一个半月就仓惶离京,败逃南去,刚刚宣告成立的大顺王朝灰飞烟灭。
文章发表时,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后期。毛泽东在4月对整风运动作总结的《学习和时局》中说:我们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个星期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将它作为整风文献推荐全党干部学习。这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感谢此前郭沫若来信对党的抗战路线和延安成为民主圣地的夸奖。他写道: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我将其称之为“甲申对”。
再谈谈“窑洞对”。1945年7月初,党的七大闭幕20天后,代表中间势力的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6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延安由最初2000人发展到5万人的巨大变化。其间,毛泽东同黄炎培有一次长谈。毛主席问他访问后有何感想?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明确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毛泽东为什么明确回答中国共产党能跳出“周期率”呢?一是我们党的先进性使然,就是坚持党的初心,初心变恒心,就有这个可能;二是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对党的建设所发生的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党的七大表现的高度民主活泼氛围和团结友爱真情,使毛主席很受感动。一些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主动作自我批评,博古的发言还博得大会热烈鼓掌。最后选举中央委员会,毛主席多次讲话,要选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包括王明。许多代表想不通,毛主席让各代表团做工作。在唱票时,直听到王明的得票超过半数,他才离开会场。七大这样广泛地大团结,获得空前成功。所以,毛主席回答黄炎培的“周期率”问题,信心满满地说:我们找到了能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甲申对”和他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甲申对”深刻揭示了李自成大顺农民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李自成农民军打天下18年,坐天下42天,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典型表现。李自成农民军为什么灭亡得这样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骄傲腐败。共产党的成分也有很多农民,黄炎培在延安考察后对共产党佩服,但仍然担心能否跳出“周期率”。黄炎培提出问题是善意的,毛泽东充满底气的回答令他信服。他在回重庆后写的《延安归来》中说:“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正因为他相信共产党能跳出“周期率”,这也是他后来参加新政协,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应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一个重要考量。
毛泽东关于“赶考对”与“两个务必”是同时提出的。从前述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将两者放在一起讲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赶考问题讲的较多,“赶考对”成了热门话题。70多年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赶考对”的大背景,是中共中央正在筹建新中国。筹建新中国主要是通过两个会进行的,即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在九月会议上决定从1946年7月算起的大约5年左右时间,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立即进行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邀请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共商国是,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临时中央政府,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主题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全会着重讨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党的工作重心实行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要求全党学会管理城市,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二是关于经济政策,明确建国后有五种经济成分,对待不同经济成分采取不同政策。三是关于在全国解决土地问题后的两种基本矛盾问题(即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的为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四是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次全会对筹建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基本安排就绪。会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在出发作准备时,毛泽东对周围同志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3月23日启程进京,毛主席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现在称“赶考对”。
“赶考对”显然是回应“甲申对”的。从“甲申对”到“窑洞对”,再到“赶考对”,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以李自成农民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周期率”为史镜,共产党绝不能再重蹈覆辙,成为20世纪的李自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不能说没有。不仅黄炎培担心,其他人也在担心。1948年12月,辽沈战役已结束,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大局已定,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他还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刘少奇非常尖锐讲的这个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讨论了。毛主席讲的“两个务必”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务必”也是回答三次“重要对谈”所提出的问题的。
三次“重要对谈”和“两个务必”思想,虽然是70多年前的往事,但具有永不过时的警示和启迪意义。腐败亡党亡国,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凡被推翻的政权,无不是腐败使民心丧失殆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这始终需要我们党高度警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上就是在新时代条件下来回答三次“重要对谈”提出的问题。怎样防治腐败?至少有四点:一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炼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两个务必”思想,牢记骄躁非败即挫,诚恐戒惧永不松懈;三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民主新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四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反腐败斗争,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使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成为有口皆碑的常态。